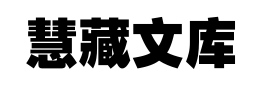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5-03-22 17:46:37
一位耶鲁佛学博士的佛学研究之路(八)
来源:http://manyuer.bokee.com 作者: 王翔
四、港大佛学中心第一学期日志(2003年10月)
31日:我埋首工作了一天,不过也听了不少曲子,最欣赏的是“十二国记”原声大碟中最有名的那首“风骏”,这名字光听起来就颇有诗意,这种流畅的具有古典风格的曲子让自己的感性神经保持兴奋。其实在学习中我会常常看些动画片,魔幻小说什么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让经由文学培养起来的感性的细胞迟钝了。今天晚上出门一看,才发觉已经是万圣节了,我有时候也会叹一口气,似乎自己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在这离世间遥远的地方所体味到的乐趣和美感又有谁人知呢,我们在历史中的旅行同样也为我们在千山万水间的真实旅行做好了准备。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下个月将是严格的写作的时间,我的计划是:星期二,三,五,六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全部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写作,中间下午两点去吃饭;星期一,四,日因为有课,安排为中午11点半吃饭,下午在图书馆study room, 直到5点30去吃晚饭,星期天一天都是学习梵文的时间。
28日:只要去图书馆总要在第一层看看新书,有那么一瞬间,觉得非常的自由了,就像是回到了随意读书的本科时代,时间如流水一般,眼界也没有限制。当时可以关注文史哲所有感兴趣的领域的新书,当然因为图书馆的限制,文本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如今天。
26日:有的时候,理性的书看久了,也想舒舒服服读些幻想小说,换换胃口,我尝试了一下,我得承认,有一些网上的小说还真的是很精彩的。比如名作“天魔神谭”,这部书真的充满了梦幻色彩,非常好看。一开始几章中,最让我感动的情节是御莱斯达克将军为了让的四个儿子和老父亲逃出原曙城,抱着玉碎的决心做绝死一战,独自抵挡40多个身手不凡的敌人,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依然击杀了20余个劲敌。这时心脏粉碎,生机已绝的御莱凭着最后一口气,使用太古魔导法,准备与最后的三个敌人同归于尽,这一击在一瞬间如同烈日一般照亮了黑夜,这一刻也因此而成为原曙城“黑夜烈日”的传说,但终于因为能量过大,使他的身体化为黄金一般的尘埃慢慢地消逝在夜风里。那最后幸存的三个敌人也因为他神一般的英勇气概而在他随风消逝的地方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而这之后的两年,御莱舍身战死的地点成为一个人和动物都无法接近的禁区,聚集了浓厚的土元素。只到两年之后,他的儿子亚在悲愤中回到这一地点,才重新找到了父亲在最后一刻留下的记忆和不灭的精魂。所以尽管这是一部通俗的作品,我得承认,这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情节让人回味。
25日: 其实现在很忙,但是宋美龄去世了,似乎应该说什么吧。我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没有专业级的知识,但是在10年的读书生涯中,对于中国的最近150年,我看到的是一个激荡宏伟的画面。宋美龄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传奇的历史。宋美龄的死让我们对于人生的争斗和执着有了更清晰的醒查,在我的心里更滋长了看遍世事之后的一丝虚无。我在古都南京,新都北京都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在天安门的晴空下,在总统府的长廊中常常能够回忆起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在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了,这些历史的沉思也和我的个人史,个人的学习史联系在一起了,如今我一个人在异乡求学,在离开南京6年之后依然在学术的道路上跋涉,有一种“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感觉,但是回想起在河海稚嫩的求学时代,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无畏的纯真年代。然而这一切尽管美丽,不也如同梦一样吗。
20日:在港大呆了一段时间了,我暗自能够感到,港大是以西方为模式的很优秀的学校,有很完善的条件和财力,但是这毕竟是地域性的大学,它的背景和腹地太有限,这使得它无法拥有一种大气。无论是北大还是耶鲁,都有其自己不可言喻的大气,北大尽管在很多硬件和财力上不如港大,但是它毕竟是以广阔的中国为腹地,它集中了全中国的最优秀的学生,它代表了一个大国的学术雄心和历史缩影,所以就长远的眼光来看,我总是觉得北大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它一定会超过任何地域性的大学而成为中国真正的学术王座。
12日: 学习固然是漫长而又严格的训练,但是这同样是一种充实和趣味盎然的生活,是一种发展内在的挑战。就像习武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培养成一流高手,职业棋手不断磨练力图跻身九段的行列。同样,在真正的一流的大学,博士的训练固然漫长,但是它的严格的确让人受益良多,它的全方位的从语言到知识面到眼界的训练使得候选人慢慢地展现了一种博学多才的美,他不断地深入到一片海洋中去,如同舞者沉浸在自然流动的形体的动作之中。
10日:有的时候觉得印度的古代文学充满了神性,而且诗意盎然,有着一种宁静的美,比如北大的毕业生会得到一张校友卡,关于这张校友卡的介绍就引用了迦梨陀娑(Kalidasa)的Abhijnansakuntala“沙恭达罗”中的诗句。同样今天在纪念季羡林先生的文集中也看到迦梨陀娑的诗句。
8日:好像很久的时间没有过快意恩仇的生活了,有的时候会非常地怀念。在深夜无人的时候,我还能回忆起少年时清澈的理想,想起来似乎是不久的过去但是已经完全不再的本科时代的回忆。
7日:普林斯顿确实是有着极其好的条件,能够为学生提供5年的全奖,就这一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啊。东亚系的陆扬先生问我问什么选择去香港大学,我在信里面用中文回答如下:
我转向佛学其实也只有1年零9个月,所以在耶鲁的时候也错过了weinstein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课程,之后耶鲁就没有了固定的佛学教职,后来只是来了两个短期的访问教授。所以去年申请的时候,我只递交了几所学校,觉得准备得并不充分,也没有比较成熟的sample, 尽管我也申请了普林斯顿的宗教系,但没有成功。录取我的学校,比如伊利诺大学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在美国,同时有财力和师资支持学习中国佛教的学校本来就寥若晨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耶鲁的学习压力颇大,非常疲劳,所以我更愿意用1-3年的时间作充分的准备,喘一口气,慢慢地积累,而且尽管我读书不曾懈怠,以泡一流的图书馆为乐趣,以自由的大学为终生的归宿,但是我也要考虑个人的生活,在美国攻读佛学博士,年深日久,语言和养的训练漫长,食品难以下咽,如果没有F2的支持真的是难以为继。所以到香港大学作为中转站,可是说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的结果。而且在这里也有一些耶鲁所没有的佛学书籍,从参学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博采众长。
4日:今天尝试翻译梵文的几个短句,据我的观察是选自古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Mahabharata),梵语如此的复杂,学起来真的是很难啊,不过学任何的语言都不容易,明天下午梵文课,所以干脆一天都用来学习语言了。
3日:在图书馆里看各种画册,在伯孜克里卡的图片中似乎找到了迦楼罗(Garuda)的形象, 在敦煌壁画中好像也有,看来要花时间去浏览所有石窟全集了,从四川到中亚地区的巴米扬,不过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后来看了最新的两期《中国国家地理》,四川的图片真是美极了,关于甘肃长成的一张照片勾起了我对于当年路过的河西走廊的美好回忆。照片里的地方我亲自经过,而且那天晴空万里,我打前站,在辽阔无垠的戈壁大地上飞驰,身心似乎都得到了解放,真的非常怀念,等我有时间的时候,重新回忆并写出当年的所有的经历,题目就叫做 “大西北的苍茫时刻”。
2日:借了一本哈佛的照片集(Harvard: A Living Portrait),看了前言,是从11000多张照片中选出了100多张,确实是非常的精彩。我复印了几张贴在书桌前的小板子上,其中印象深刻的一张,是一位教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展读藏文典籍的场景,他坐在两排书架之间,架子上是一排排一层层用黄布包起来的藏文佛经,就像我在西藏看到的那样。本书的编者是哈佛音乐系毕业的,他在前言的最后写了一段很精彩的对哈佛的总结,我看了很感动,特意摘录如下:
Harvard has given great men and great ideas and great citizens and great teachers to the nation; she has seen us through nearly a dozen wars. She has given us six presidents of our country; she has stood like a rock in our midst. She has weathered criticism just and unjust, and abuse which is never just; she has 1ooked at her own faults, which have been not a few, and has strived to correct them. She is far from perfect, but she knows that perfec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perpetual will to seek it. If she was ever the rich man’s college, she is just as much the poor man's college today; for her sole requirement of the entering student is that he or she have character, ambition, 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to learn to think for himself----for her self. She is not prejudiced with respect to race or creed or color. She is able and eager to help those who enter her gates. She is anxious to be one thing above all: a better Harvard tomorrow than she was yesterday. To that end, she is permanently for change but always with an eye to the unchanging values of the human spirit. Lastly and most important, she has faithfully stood for the freedom of the mind and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the strange abrasive period which has followed World War II. As one alumnus once wrote to my office: This gift is "for the institution that represents one of th great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
David McCord
来源:http://manyuer.bokee.com 作者: 王翔
四、港大佛学中心第一学期日志(2003年10月)
31日:我埋首工作了一天,不过也听了不少曲子,最欣赏的是“十二国记”原声大碟中最有名的那首“风骏”,这名字光听起来就颇有诗意,这种流畅的具有古典风格的曲子让自己的感性神经保持兴奋。其实在学习中我会常常看些动画片,魔幻小说什么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让经由文学培养起来的感性的细胞迟钝了。今天晚上出门一看,才发觉已经是万圣节了,我有时候也会叹一口气,似乎自己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在这离世间遥远的地方所体味到的乐趣和美感又有谁人知呢,我们在历史中的旅行同样也为我们在千山万水间的真实旅行做好了准备。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下个月将是严格的写作的时间,我的计划是:星期二,三,五,六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全部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写作,中间下午两点去吃饭;星期一,四,日因为有课,安排为中午11点半吃饭,下午在图书馆study room, 直到5点30去吃晚饭,星期天一天都是学习梵文的时间。
28日:只要去图书馆总要在第一层看看新书,有那么一瞬间,觉得非常的自由了,就像是回到了随意读书的本科时代,时间如流水一般,眼界也没有限制。当时可以关注文史哲所有感兴趣的领域的新书,当然因为图书馆的限制,文本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如今天。
26日:有的时候,理性的书看久了,也想舒舒服服读些幻想小说,换换胃口,我尝试了一下,我得承认,有一些网上的小说还真的是很精彩的。比如名作“天魔神谭”,这部书真的充满了梦幻色彩,非常好看。一开始几章中,最让我感动的情节是御莱斯达克将军为了让的四个儿子和老父亲逃出原曙城,抱着玉碎的决心做绝死一战,独自抵挡40多个身手不凡的敌人,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依然击杀了20余个劲敌。这时心脏粉碎,生机已绝的御莱凭着最后一口气,使用太古魔导法,准备与最后的三个敌人同归于尽,这一击在一瞬间如同烈日一般照亮了黑夜,这一刻也因此而成为原曙城“黑夜烈日”的传说,但终于因为能量过大,使他的身体化为黄金一般的尘埃慢慢地消逝在夜风里。那最后幸存的三个敌人也因为他神一般的英勇气概而在他随风消逝的地方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而这之后的两年,御莱舍身战死的地点成为一个人和动物都无法接近的禁区,聚集了浓厚的土元素。只到两年之后,他的儿子亚在悲愤中回到这一地点,才重新找到了父亲在最后一刻留下的记忆和不灭的精魂。所以尽管这是一部通俗的作品,我得承认,这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情节让人回味。
25日: 其实现在很忙,但是宋美龄去世了,似乎应该说什么吧。我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没有专业级的知识,但是在10年的读书生涯中,对于中国的最近150年,我看到的是一个激荡宏伟的画面。宋美龄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传奇的历史。宋美龄的死让我们对于人生的争斗和执着有了更清晰的醒查,在我的心里更滋长了看遍世事之后的一丝虚无。我在古都南京,新都北京都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在天安门的晴空下,在总统府的长廊中常常能够回忆起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在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了,这些历史的沉思也和我的个人史,个人的学习史联系在一起了,如今我一个人在异乡求学,在离开南京6年之后依然在学术的道路上跋涉,有一种“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感觉,但是回想起在河海稚嫩的求学时代,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无畏的纯真年代。然而这一切尽管美丽,不也如同梦一样吗。
20日:在港大呆了一段时间了,我暗自能够感到,港大是以西方为模式的很优秀的学校,有很完善的条件和财力,但是这毕竟是地域性的大学,它的背景和腹地太有限,这使得它无法拥有一种大气。无论是北大还是耶鲁,都有其自己不可言喻的大气,北大尽管在很多硬件和财力上不如港大,但是它毕竟是以广阔的中国为腹地,它集中了全中国的最优秀的学生,它代表了一个大国的学术雄心和历史缩影,所以就长远的眼光来看,我总是觉得北大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它一定会超过任何地域性的大学而成为中国真正的学术王座。
12日: 学习固然是漫长而又严格的训练,但是这同样是一种充实和趣味盎然的生活,是一种发展内在的挑战。就像习武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培养成一流高手,职业棋手不断磨练力图跻身九段的行列。同样,在真正的一流的大学,博士的训练固然漫长,但是它的严格的确让人受益良多,它的全方位的从语言到知识面到眼界的训练使得候选人慢慢地展现了一种博学多才的美,他不断地深入到一片海洋中去,如同舞者沉浸在自然流动的形体的动作之中。
10日:有的时候觉得印度的古代文学充满了神性,而且诗意盎然,有着一种宁静的美,比如北大的毕业生会得到一张校友卡,关于这张校友卡的介绍就引用了迦梨陀娑(Kalidasa)的Abhijnansakuntala“沙恭达罗”中的诗句。同样今天在纪念季羡林先生的文集中也看到迦梨陀娑的诗句。
8日:好像很久的时间没有过快意恩仇的生活了,有的时候会非常地怀念。在深夜无人的时候,我还能回忆起少年时清澈的理想,想起来似乎是不久的过去但是已经完全不再的本科时代的回忆。
7日:普林斯顿确实是有着极其好的条件,能够为学生提供5年的全奖,就这一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啊。东亚系的陆扬先生问我问什么选择去香港大学,我在信里面用中文回答如下:
我转向佛学其实也只有1年零9个月,所以在耶鲁的时候也错过了weinstein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课程,之后耶鲁就没有了固定的佛学教职,后来只是来了两个短期的访问教授。所以去年申请的时候,我只递交了几所学校,觉得准备得并不充分,也没有比较成熟的sample, 尽管我也申请了普林斯顿的宗教系,但没有成功。录取我的学校,比如伊利诺大学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在美国,同时有财力和师资支持学习中国佛教的学校本来就寥若晨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耶鲁的学习压力颇大,非常疲劳,所以我更愿意用1-3年的时间作充分的准备,喘一口气,慢慢地积累,而且尽管我读书不曾懈怠,以泡一流的图书馆为乐趣,以自由的大学为终生的归宿,但是我也要考虑个人的生活,在美国攻读佛学博士,年深日久,语言和养的训练漫长,食品难以下咽,如果没有F2的支持真的是难以为继。所以到香港大学作为中转站,可是说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的结果。而且在这里也有一些耶鲁所没有的佛学书籍,从参学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博采众长。
4日:今天尝试翻译梵文的几个短句,据我的观察是选自古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Mahabharata),梵语如此的复杂,学起来真的是很难啊,不过学任何的语言都不容易,明天下午梵文课,所以干脆一天都用来学习语言了。
3日:在图书馆里看各种画册,在伯孜克里卡的图片中似乎找到了迦楼罗(Garuda)的形象, 在敦煌壁画中好像也有,看来要花时间去浏览所有石窟全集了,从四川到中亚地区的巴米扬,不过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后来看了最新的两期《中国国家地理》,四川的图片真是美极了,关于甘肃长成的一张照片勾起了我对于当年路过的河西走廊的美好回忆。照片里的地方我亲自经过,而且那天晴空万里,我打前站,在辽阔无垠的戈壁大地上飞驰,身心似乎都得到了解放,真的非常怀念,等我有时间的时候,重新回忆并写出当年的所有的经历,题目就叫做 “大西北的苍茫时刻”。
2日:借了一本哈佛的照片集(Harvard: A Living Portrait),看了前言,是从11000多张照片中选出了100多张,确实是非常的精彩。我复印了几张贴在书桌前的小板子上,其中印象深刻的一张,是一位教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展读藏文典籍的场景,他坐在两排书架之间,架子上是一排排一层层用黄布包起来的藏文佛经,就像我在西藏看到的那样。本书的编者是哈佛音乐系毕业的,他在前言的最后写了一段很精彩的对哈佛的总结,我看了很感动,特意摘录如下:
Harvard has given great men and great ideas and great citizens and great teachers to the nation; she has seen us through nearly a dozen wars. She has given us six presidents of our country; she has stood like a rock in our midst. She has weathered criticism just and unjust, and abuse which is never just; she has 1ooked at her own faults, which have been not a few, and has strived to correct them. She is far from perfect, but she knows that perfec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perpetual will to seek it. If she was ever the rich man’s college, she is just as much the poor man's college today; for her sole requirement of the entering student is that he or she have character, ambition, 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to learn to think for himself----for her self. She is not prejudiced with respect to race or creed or color. She is able and eager to help those who enter her gates. She is anxious to be one thing above all: a better Harvard tomorrow than she was yesterday. To that end, she is permanently for change but always with an eye to the unchanging values of the human spirit. Lastly and most important, she has faithfully stood for the freedom of the mind and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the strange abrasive period which has followed World War II. As one alumnus once wrote to my office: This gift is "for the institution that represents one of th great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
David McCord
本文有『居士林网』jsl.com.cm提供整理和服务器存储